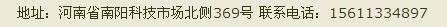迟放鲁每个人都能听见花开的声音
二四一
这是一次旷日持久的
寻医之旅
晔问
问尊严,问名声
问灵魂,问态度
……
READON「迟放鲁
每个人都能
听见花开的声音
」人物介绍
迟放鲁,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年出生,医学博士,现任复医院副院长、耳神经颅底外科主任,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医学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擅长人工耳蜗植入治疗双耳全聋、各种中耳炎和耳硬化症患者的耳聋的听力重建、周围性面瘫和眩晕的内科和显微手术治疗、耳鼻区颅底外科治疗听神经瘤及侧颅底肿瘤。目前从事全植入式人工耳蜗研究和内耳毛细胞再生的研究。主持和参与的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成果奖15项。完成国家十五攻关项目和国家十一五支撑项目各1项、国家自然基金4项。获国家发明专利5项、申请4项。
中国中西医学会耳鼻喉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师协会耳鼻喉科分会会长,曾任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头颈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学会耳鼻喉科分会副会长。“JournalofOto-Rhino-Laryngol,HeadNeckSurgeryORL”杂志国际编委。美国AAO-HNS协会国际会员,HearingInternational国际会员。《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主编。
采访笔记“耳科手术,就是在刀刃上的芭蕾,稍一闪失,面神经坏了,眼睛闭不上了。耳朵里的手术,由于面神经埋藏在耳朵的骨结构中,看不见又伤不得,考验的是经验阅历,定位精准。所以没几个医生愿意做耳科手术,在耳鼻喉科医生中,耳科手术医生最多只占十分之一。我对年轻医生们说,别刚开了几十刀就想上天了,我做了四百台手术,才刚刚入门,直到一千台,才基本稳定了,没有一万小时的锤炼,做不了手术医生。”他还记得第一台手术,从头顶凉到脚心,大气不敢喘,而现在,面神经都听他指挥。
医院副院长,耳神经颅底外科主任、上海市听觉医学临床中心主任,教授迟放鲁医生,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喉科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师协会耳鼻喉科分会会长。曾任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学会耳鼻喉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上海市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擅长人工耳蜗植入治疗双耳全聋、各种中耳炎和耳硬化症患者的耳聋的听力重建、周围性面瘫和眩晕的内科和显微手术治疗、耳鼻区颅底外科治疗听神经瘤及侧颅底肿瘤。
“那个女孩,十年前给她做了人工耳蜗,六月一日,她的生日,手术也是这天做的,她妈妈说,这是重生。”女孩如今与常人无异,一样的听说读写,一样的古灵精怪,她把耳蜗用密密的长发遮掩起来,心事也随着藏的严严实实。后来他问女孩,你喜欢头上这个东西吗?女孩一噘嘴,不喜欢,为什么别人没有呢。这句话,一半是撒娇,一半却真的撞在他的心上,于是接下来的十年,他组建团队,开发研究“全植入人工耳蜗”,如今初有成绩,朝着实用迈出了一大步,“最终目标是植入人工耳蜗后在患者外表看不出痕迹,让他们与正常人无异。”
他从小就喜欢机械,动手能力过人,当过汽车修理工,能把一辆三轮摩托车大卸并完好组装,他对这样的经历是否与他今后的发明有关,他不置可否,“其实,有两种医生,一种只是临床,另一种是临床与科研并进,我属于后者,对医学研究的兴趣是推动医学发展的动力。”
当年,中国耳科显微外科泰斗王正敏院士将人工耳蜗植入的技术传授给了迟放鲁。“这是改变人生命运的手术,让一个失聪的,对生活恐惧,只敢在小圈子里过营生的人,回归社会,回归自信,脱胎换骨,医生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无以复加。”
从第一例手术至今,人工耳蜗他做了二千多例,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一连串的社会效应:经过同行点努力。上海户口六岁以下的聋孩,95%经过医治,回到正常轨道;政府补贴由6万元逐步增加到13万元,接近于免费手术;甚至是缴纳上海社保的外来人员,也能享有同样待遇。“当初筚路蓝缕,装了人工耳蜗的孩子,学校还不敢接纳,生怕发生意外,但孩子们必须在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得到训练。我通过各种渠道呼吁,终于得到社会点响应,如今植入人工耳蜗的孩子都能够到正常幼儿园和正常学校上学了。”
一直在忙碌,一辈子都在忙碌,他自己都担心,一旦退休,真的闲下来,他能干点啥,“时间都在刀尖上溜走了。”
直到前几年,医院最晚离开的人,他住在东平路,午夜11点踩着星斗走在上海的桃花源上,周围梧桐葱茏,庭院幽深。“从岳阳路到衡山路短短的百十米,那些旧上海花园别墅,掩映在庭院中,显露出沉郁的贵族气质,雅致、安逸、静谧。其实做医生,追求的也是这样的气质,纵然隐姓埋名,情怀依然还在。”
走在这条路上,想着白天的手术,他的脚步轻松,内心欢喜。
1“十三所聋哑学校关门殆尽”迟放鲁说,开始的时候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如何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用得起人工耳蜗。一个人工耳蜗大概是20多万的费用,用当时的话来说,一辆桑塔纳轿车装进耳朵里去了,费用昂贵,但是明明知道这可以改变很多孩子的命运,可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装不了,可能就此错过一生使用人工耳蜗的机会,终身变成一个聋哑人,这是最让他痛苦的。
他有一个数据,人工耳蜗技术最早在国内,一年只有二十几例,等到他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全国一年也不过两三百例。之所以这么少的一个原因就是费用——用得起的家庭太少了,再有就是不相信——别说病人不相信了,连很多医生也不相信,这么一个小东西放进耳朵,聋哑人可以听见声音学会说话了?很多人都有质疑,甚至觉得是“骗人的”。“我们带着安装了人工耳蜗的病人去做宣教,被说成这是医学惯用的明星病人——十个里面治好了一个,就拿出来做典型宣传。可想而知,刚开始步履维艰,加上价格又贵,不能让病人大量免费尝试,这样的情况下推广是很难的。”迟放鲁说。
不过,迟放鲁表示,人工耳蜗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效,6岁以下的孩子如果没有学会讲话可以安装,但是8岁了还不会讲话就没办法了,因为,即使安装了耳蜗可以听见说话了,但大脑无法理解语言的意思,“听不懂了,完全无法理解,所以也没有办法和别人用语言交流,一辈子只能做聋哑人了,很遗憾。”
对此,临床的解释是,大脑有中枢神经叫听觉皮层,听觉皮层旁边还有言语皮层,刚出生时语言皮层没有发育,听到声音之后才会发育,如果8岁了还是没有听到声音,语言皮层就不会发育了,一直停留在不成熟状态,长大后对人类的语言无法识别,这就是为什么看着很多孩子本来有机会摆脱聋哑人的命运,结果错过了,这时候别说医生,所有人都会很惋惜。
“全世界都一样,从疾病角度看,最大的残疾人群体是聋哑人。在我国,聋孩的出生概率是千分之二,全国本来每年有2万人成为聋哑人,有了人工耳蜗,这个群体逐渐萎缩,上海过去有13所聋哑人学校,现在只有几所还存在在,主要收外地孩子。上海的孩子都做了人工耳蜗,都到正常学校去了。人工耳蜗改变了这些孩子的人生,也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家庭。”迟放鲁说。
事实上,迟放鲁是这桩大事最早的推动者之一,作为专业人士参与标准制定,如今倍感欣慰。“今年全国人工耳蜗手术每年可以达到例,上海估计有个孩子在使用人工耳蜗。能做到这些,真的要感谢很多人——最早是台湾王永庆先生捐献了很多人工耳蜗,后来是很多慈善机构;更应该感谢的是政府的推动,年起,本市户口每一例6岁以内的孩子安装人工耳蜗,都由残联出资补贴,最早是六万元,现在是13万元,等于一个单侧人工耳蜗的费用。这样的话,有的家庭自己出钱做了双侧耳蜗,交流起来和正常人一模一样。近两年的政策更好,外地人员在上海工作,只要交了社保,孩子在上海出生,有上海的出生证,也能享受这个待遇。”
迟放鲁坦言,医院为了配合这个项目,曾免掉了患儿做手术的住院费,手术费和一些医药费用进医保,病人自费费用已经很少了——技术发明出来不算什么,真正用到临床上让病人获益才是医学的目的,“我想让每个人都听得见。”
2成就感来自开口说话的孩子迟放鲁,出生镇江,15岁当兵,在南京军区当了六个年头的军人,22岁转业当了一名修车工。年国家恢复高考,24岁的他靠自学考取镇江医学院,一所当时的专科院校。“当时填报的所有志愿,就只有这个志愿录取了,学校离家又近,也就没什么选择余地。毕业后分配医院,当耳鼻喉科医生。”
说起之所以选择耳鼻喉科,也是无心插柳,在大学里,他是学生会主席,表现优异,是唯一一个留校的,当时耳鼻喉科缺人就让他去了,工作五年后,他读了硕士,回去工作五年,又读了博士。
“很幸运,读书那些年,遇到了几位好老师。一位是第二军医大学耳鼻喉二级教授肖轼之主任,我跟了他三年,改革开放前一半的耳鼻喉临床教材是他编写的。”迟放鲁回忆,肖轼之老师个子不高,待病人和蔼,但是非常严谨,老师的理论知识惊人,凡事都讲依据,“他说一个要点,在哪本著作可以查到,我们一查,果然都能找到。”
从肖轼之老师身上,迟放鲁悟出,医学除了经验的积累,还要不断学习——翻阅大量书籍、资料,思考整理案例等。肖老医院,在实验室烧好开水,就看书,查完房又去看书,每周给大家讲一次课,用毛笔在报纸上书写,字迹漂亮,“他是当时医学界公认的秀才,还是第二军医大学报的主编,人文素养高,擅散文,也写人物传记,老先生除了有才学,还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迟放鲁在肖老师的耳提面命下成长,他记得老师常说,做医生不是单纯开好刀,而是要把问题搞明白。跟着老师,学着老师的方法,他渐渐觉得耳科的神秘和兴趣,“老师查体,一定不会光查耳朵,还要检查鼻子和咽喉,一定是把这几处查完了才做结论,现在我也这样。绝对不会草草下结论。”
医院,中国耳科显微外科泰斗王正敏教授是迟放鲁的另一位恩师。王教授是中国耳科显微外科的开拓者,年公派到瑞士学习——那里有全球最高级别的耳科显微外科专家。回国后在艰苦的条件下做的国内第一台耳显微手术,“那时候国内显微镜跟不上,他得小心翼翼,他是国内第一个做中耳炎手术的人,业界公认的泰斗。”
王教授培养迟放鲁的过程别具一格,有四个阶段,每三个月让迟放鲁做一台新手术,“第一台手术,是他的病人让我开刀;第二台手术,是让我自己收治一个病人,他在一边看我做;第三台手术是我主刀,他不出现,医院;第四台手术,才是我完全独立。教授思维严谨缜密,作为后来者是幸运的,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感谢他把所有的收获都传承给了我们。”
3时间都去哪儿了这么多年,迟放鲁说,耳科手术的经验就是记住结构位置,在看不到的情况下定位,“找到几个坐标,让这几个坐标告诉你怎么走,虽然看不到,但是你知道怎么操作。如果把手术比喻成雕刻,这就是盲雕,并且不允许修改,不能有丝毫闪失。我告诉学生,做过个手术才开始有感觉,有人觉得开了上百个手术了不起了,其实每个病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碰到标准的病例以为自己过关了,这不行,一定要碰到形形色色的病例,才能算有了一点经验积累。”
千锤百炼,迟放鲁掌握了老师的精髓,他笑称,耳朵手术在耳鼻喉里是最难的,全国现在也不过三万名耳鼻喉科医生,而很多人不愿意做耳科医生,因为手术只能做到中耳,内耳看不到,凭立体解剖经验和技能做手术,“在钢丝上跳舞,面神经就是钢丝。我们看不到内耳,其他手术有些神经可以解剖出来,但是耳朵神经埋在骨头里面,没有经验碰到一点就伤到了,这是最难的,很多医生怕做这个手术。”
两个导师跟下来,迟放鲁越来越喜欢耳科。至今他做了2台人工耳蜗手术,每年在台左右,但是他说自己还是在变化,尽量让手术越来越简洁。“每个医生有自己的风格,没有人能说自己的风格是最好的,但是适合这个医生的就是最好的。”
迟放鲁的病人中,大多数是需要装人工耳蜗的患儿。他说,发自内心喜欢这些孩子。“医生和其他的职业不太一样,做医生太需要成就感了——医学上真正能治愈的疾病并不多,能彻底治愈的可能就是大叶性肺炎。现在医学进步了,但是治愈率和死亡率并没有太大改变,只是治疗手段改进了,面对死亡的时候,医生感到更多的还是无奈,是跟病人一样的绝望。但是人工耳蜗不一样,本来是一个充满恐惧和自卑的聋哑孩子,安装人工耳蜗后,会说话了,到正常学校去上学了,长大后结婚生子,因着自己的手改变了残酷的命运,做医生太有成就感了,太幸福了。”
他记得,以前孩子们会讲话以后,来看他时都叫他叔叔,现在那些孩子都叫他爷爷了,“一晃二十几年,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溜走了,却留下他人生中是最绚烂的一笔。
4全植入人工耳蜗迟放鲁的传奇还没有结束。
早些年有个上海的小姑娘,她母亲恳求迟放鲁,希望能在六月一日那天做人工耳蜗手术,那天是孩子的生日。“我应允了,小姑娘机灵可爱,她把耳蜗伪装成一个装饰品,女孩子长头发,耳蜗掩在头发里,根本看不出来,现在已经10岁了,说话和正常人一样。”迟放鲁记得问她一句话:你喜欢这个吗?孩子说,不喜欢,别的小朋友都没有就我有,小孩子的实话让迟放鲁难受。这件事他一直记在心上。
能不能把耳蜗装进耳朵里去?10年前,他就有了这个想法,“全植入人工耳蜗”,这一做就做了10年,做到今年才算把基本的框架做完。一个关键点是,要有可充电的电池,隔着皮肤充电,现在,这样的电池出现了;另一个关键点是,要把麦克风植入到耳朵里,要做到非常小,难度就在这里。迟放鲁的想法是,在中耳的听骨上加上一个传感器,这个传感器把耳膜的震动变成电流,再送到植入在耳朵里的芯片上,通过芯片处理送到内耳。去年在志愿者身上做了实验,确实能将听骨的振动信号取出,但是做不了电学的实验,最近拿到美国的实验室去做。“最重要的是idea,核心的东西是自己做,外围的是国外的公司帮着做。”迟放鲁说。
他说,这些和自己之前工人出身大有关系,什么坏了都是自己修理,当兵的第一年部队给了他一辆摩托车,坏了他就自己修理,自己换零件,现在还可以把摩托车全部拆开,自己重新安装。
“科研是乐趣。为什么我当初承诺,能把老师的技术传承下来,就是能在科研里找到乐趣。我更喜欢把临床和科研结合起来,让医学走的更远。”
口述实录
晔刚开始做完人工耳蜗,是不是还要帮助孩子适应社会?迟放鲁过去,戴助听器的孩子,由于听力没有补偿,都是在聋校里学习,这些孩子学会简单讲话,但是还是和聋哑孩子在一起,毕业后还是上聋哑学校,并没有真正融入到正常生活中去。人工耳蜗植入植入后听力补偿了,有了学习讲话点能力,但是还是要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十年前,我们问过一些幼儿园,这些孩子进不去正常幼儿园,没有学校敢收——小孩子之间要打闹,撞来撞去的,一个东西二十几万,撞坏了怎么办/幼儿园不收,我们就向媒体、向教委呼吁,教委要求学校必须接受,同时教委向学校里配备一个辅导老师。现在,所有的学校都可以正常接受这些孩子。晔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要做双侧人工耳蜗,这里的区别是?迟放鲁单侧耳蜗和双侧相比有很多不足,一是声音单调——单声道和双声道的区别;二是没有方向感;三是对音乐分辨不清——能听懂音乐的主旋律,但是分不出小提琴和贝斯这些乐器的声音,没有丰富的层次感;四是走到街上吵闹的地方,就听不清楚。所以,在经济实力许可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做双侧。晔您觉得已经超过王正敏教授的技术了吗?迟放鲁导师的手术登峰造极,自己远远比不上。百人计划擂台的时候,当时有人被问能不能超过导师的技术,我那时就说,虽然我做不到,但是我们有这么多人,可以完全把导师的技术传承下来,我们现在有五个师兄弟,一个团队,除了继承老师的技术,也在尝试新的东西,医学要不断发展。晔您在手术台上是什么感觉?迟放鲁现在是一种乐趣,每台手术都很轻松,不像当初的时候,手术结束先着急看看病人的眼睛,如果眼睛闭上了,说明面神经没问题,那就没事了。晔您喜欢医生这个职业吗?迟放鲁做医生非常难,医学不能像机器一样,标准化地修理好,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看问题的方法,在几十年后看,或许都是错的。但是,在这种有争议的情况下,医学还是拯救了很多人,医学有自身矛盾的地方,谁都没办法改变。有人把医学完全当成商品。其实,没有几种病是真正可以完全治愈的,医生只能让很多病好转、稳定。医疗环境不好,很多医生已经放弃了理想,但是我还是很自豪的。晔有自己的爱好吗?迟放鲁没有什么爱好,最近爱上摄影,还没入门。晔生活中,您是个有趣的人吗?迟放鲁我还是很有趣的,喜欢开玩笑,医院里最晚走的人,医院来了,年轻人如果想走得快一点,就在下班后的时间里。晔这么忙,家人会怪您吗?迟放鲁她最担心的是我的身体健康。我太太也是医生,同班同学,我的人生完全是被她推着往前走的,从读书的时候到现在。她原是镇江的神经内科医生,学科带头人。来到上海后,为了支持我,她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支撑着整个家庭。她是我的精神支柱,一直伴我前行。人生得此伴侣,足矣。晔您觉得,医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迟放鲁是救人,我做人工耳蜗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没有救命,而是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轨迹。救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像肿瘤,检测和治疗的手段越来越先进,但是大多数时候能做的都是减轻病人的状况,医学是尽力而为的救治。晔您会焦虑吗?迟放鲁从来不会焦虑,也不会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失眠。晔如果重来一遍的话,您还会选择做医生吗?迟放鲁我还是会选择做医生,但是,我想做个精神科医生,这又是一个充满神秘的领域。采访/晔问仁医编辑/晔问仁医
晔问仁医已入驻知乎专栏、今日头条、腾讯媒体开放平台,欢迎前往订阅。
如有相关问题需要提问此医生,
或有感而发,
请在文章最下方评论区留言。
版权声明:本文系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在[晔问仁医]后台留言;
授权使用请注明:“来源[晔问仁医]及作者”。
晔问仁医真实,真切,真相长按
转载请注明:http://www.popkd.com/wacs/136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