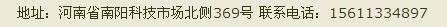荒唐的私摄影与私写真
导读:私摄影在摄影圈人人皆知,但知道来龙去脉的去很少,也造成不少误解,有人甚至一直以为中国摄影圈的所谓“私房”摄影才是私摄影。本文系统考证,深度挖掘出来“私摄影”的诞生。引入过程。对于摄影史有兴趣和对摄影学术研究者很有帮助。
关键词:私写真
关键人物:顾铮、饭泽耕太郎、柳本尚规、大竹昭子、荒木经惟
荒唐的“私摄影”与“私写真”
作者:GaryLi魔鬼公子
目前中国最流行、最泛滥、被误解最严重的摄影概念,莫过于“私摄影”。
经查,“私摄影”跟诸如风光摄影(LandscapePhotography)、纪实摄(DocumentaryPhotography)、新闻摄影(Photojournalism)的摄影类别不同,并没有对应的英文名称和资料。
“私摄影”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那日松主编的《中国摄影批评选集》(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年出版)收录的顾铮年写的《中国私摄影论》,定义了“私摄影”:“狭义的‘私摄影’可以是一切只为一己之私拍摄、保存影像的行为与习惯。这包括了家庭私人照片与出于个人欲望为自己的观看与欲望而制作的摄影影像。而广义的‘私摄影’,则可能是镜头的探视范围越出了个人与家庭而指向了拍摄者所愿意拍摄观看的一切领域。”(p.)
但是,顾铮并未交代“私摄影”的来历和出处。“私摄影”仿佛从天而降,落在他的文章的开头:“从早期西方摄影史看,摄影术发明后,除了那些马上就把摄影用于制作‘私摄影’图像者,可能要数那个写了文学名著《艾丽斯漫游仙境》(年)的牛津大学的数学教师刘易斯·卡洛尔了。”
“私摄影”源头暧昧不明,不知是不是顾铮提出的,有何依据。
《中国摄影批评选集》封面
顾铮发表《中国私摄影论》6年前,日本的饭泽耕太郎便于年就发表了《私写真论》(繁体中文版是黄大旺翻译、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年出版的)。
“写真”是“摄影”的日文名称。日文里的“私”不完全对应中文里的“私”。“私”在中文里有三个意思:“个人的,自己的,与“公”相对;不公开的,秘密而又不合法的;暗地里。”在日文里,“私”的主要意思是第一人称代词“我”,由“我”又延伸出了“个人的”的意思。因此“私写真”应该被翻译为“我摄影”。
《私写真论》封面
饭泽耕太郎用“主题”、“名词”、“潮流”、“概念”、“观点”、“角度”、“理论”、“性格”等词描述“私写真”,以至于令“私写真”扑朔迷离:“决定要来写‘私写真’这主题……”(p.5)“笔者过去已一再用‘私写真’这个名词……”(p.5)“笔者对于私写真这个‘潮流’……”(p.5)“而为了让‘私写真’作为更开阔的概念得以自由发展……”(p.6)“当我们从‘私写真’的观点……”(p.)“以‘私写真’角度来看……”(p.)“也是荒木‘私写真’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p.)“这种挑战不仅是摄影家突显出‘私写真’性格的方式……”(p.)
他这样解释广义的“私写真”——“不论什么样的照片,都能从中分析出赤裸裸的‘自我’。而当被摄主体改变,拍出的照片也会不同,同时如果把‘私我’换成另一个人,也就会产生不同的照片。也就是说,所有的照片都是‘私写真’,都是从‘私我’与被摄主体(现实世界)间的关系层层筛滤而成的结果。”(p.12)关于狭义的“私写真”,他认为——“狭义的‘私写真’,也就是类似家庭相簿那样,让‘私我’清楚入镜的照片,直到十九世纪末才出现”。(p.18)
还有“纯粹私写真”——“一种我=摄影=世界的超现实关系”。(p.86)
广义的“私写真”、狭义的“私写真”、“纯粹私写真”都是饭泽耕太郎自己定义的,他表示:“笔者也无意将自己的定义视为不二圭臬,相反地毋宁用比较建设新的思考,去重新审视‘私写真’的多义性与意义的延伸,因为我认为每一个摄影者,应该都以各自的方式在实践各自的‘私写真’。”(p.6)“‘私写真’是摄影家在各自的生活过程中,所呈现的各种面向,并不存在所谓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定义。”(p.)
《私写真论》充斥着饭泽耕太郎对“私写真”的个人见解,不是严谨的学术论著。他笔下的“私写真”的性质及含义均十分模糊,倘若不用“广义的”、“狭义的”和“纯粹”加以限定范围,恐怕根本无从探讨。
他认为狭义的“私写真”是十九世纪末出现的,但是没有列举具体符合定义的例子。相反,他列举的均是他认为不符合定义的例子:“像拉帝格或石塚这类的摄影家,在十九世纪末的登上摄影史舞台,为以个人视点拍摄家庭相簿的形式打架了基础。”(p.25)“不管是拉帝格还是石塚,都能轻松透过照片牵引人们的欢乐或幸福感,但是他们必定都经历过的负面感情(如恐怖、不安、悲哀、愤怒等),则很难从照片中看出来。在他们摄影作品中的‘私我’,总是带有像在舞台上演戏一般的二元性。当然,想从镜头拍不到的角度看出完全纯粹的‘赤裸裸的我’,也只是一种虚构,但是我们仍然得说,拉帝格与石塚的照片中的‘私我’,仍欠缺完全对应他们人生的真实触感。”(p.27)
那么,十九世纪末出现的狭义的“私写真”在哪里呢?
十九世纪末,“私写真”这个词还没诞生。
饭泽耕太郎认为,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私写真”这个词尚未出现:“就如同山岸或大辻在文章中所说,在一九七零年代即使有“私我的世界”或“私性”之类的名词,‘私写真’却尚未出现。”(p.35)
矛盾的是,他又称柳本尚规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了“私写真”这个词:“唯一的例外只有柳本尚规(曾任《provoke》编辑)在《同时代写真批评朝向恶意十足的视线》(相机每日,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号)这篇文章中,对于荒木经惟《感伤之旅》(自费出版,一九七一年)的批评。同一时期或许还有其他文章有过类似的表现,但笔者还是认为这是‘私写真’的滥觞”。(p.35)
既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柳本尚规提出了“私写真”,饭泽耕太郎怎么能说“私写真”这个词尚未出现呢?
“私写真”的提出者柳本尚规没有具体定义“私写真”,只是用它来批评荒木经惟的《感伤之旅》的“常见”、“无聊”、“为了打发时间”“扫兴”等特点:“《感伤之旅》是荒木经惟蜜月摄影集。重点并不在新婚蜜月,但在摄影集中,倒是满溢着世间与“太太”同行的旅途上常见的风情。无聊的车内时光,为了打发时间在公园散步,扫兴的风景名胜,数不尽的各种风情。《感伤之旅》无疑不是一本私小说,而是‘私写真’。”(p.35-36)
柳本尚规提出“私写真”是为了区别于“私小说”。
然而,饭泽耕太郎却擅自将“私写真”与“私小说”挂钩:“包括与‘私小说’相呼应的‘私写真’描写在内,柳本在发表评论的这个时间点上,应该已经敏锐地看透了荒木在《感伤之旅》中显现的表现质地。”“荒木从一九六〇年代后半到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之间的摄影作品,尤其是他实质上的第一本摄影集《感伤之旅》,宣示了日本‘私写真’的诞生。此后,‘私小说’性质的摄影,就渐渐变成了他创作活动的最主要支柱。”甚至在另一本摄影评论集《写真的思考》(黄耀进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出版)里指出:“所谓的‘私写真’即是与‘私小说’一样,以作者=私人为起点,从这样的视角来诉说、表达的摄影表现方法。”(p.21-22)
《写真的思考》封面
可见,饭泽耕太郎深深地误解了柳本尚规提出的“私写真”。
误解柳本尚规提出的“私写真”的,还有大竹昭子的《日本写真50年》(黄大旺翻译,脸谱出版社年出版)。大竹昭子称荒木经惟的《感伤之旅》“公开蜜月照,在这种脉络下最适合做为私写真的出发点。”(p.91)柳本尚规称《感伤之旅》是“私写真”的理由却是《感伤之旅》“重点并不在新婚蜜月,但在摄影集中,倒是满溢着世间与‘太太’同行的旅途上常见的风情。”
饭泽耕太郎的《私写真论》与大竹昭子的《日本写真50年》都摘录了荒木经惟的《感伤之旅》里的同一段宣言:“我再也受不了了,但这跟我的慢性格痢瓦拉中耳炎无关。时尚摄影都正在泛滥之中,照片里的这些脸、这些裸体、这些私生活、这些风景都充满了谎言,让我无法忍受下去。我的作品与他们的谎言照片完全不同。这本《感伤之旅》,既是我的爱,也是我身为摄影家的决心。但并不是说这些记录自己蜜月旅行的照片就一定是真实摄影喔。只是我从作为摄影家的起点出发、朝向爱前进,凑巧从私小说出发而已。我本来就一直想要写私小说。因为私小说非常接近摄影。”(《私写真论》,p.)(《日本写真50年》也是黄大旺翻译的,宣言部分跟《私写真论》略有出入,鉴于《私写真论》出版日期较晚,以《私写真论》为准。)
《感伤之旅》卷首的宣言原文
但是,这段宣言被饭泽耕太郎叫作“私小说宣言”,被大竹昭子叫作“‘私写真’的宣言”:“在纪伊国屋书店的负责人田边茂一的请托下,他故意‘用左手写下’一篇书信体的‘私小说宣言’,并且贴在卷首的第一页。”(《私写真论》,p.)“荒木在七〇年代的另一件大事,是‘私写真’的宣言。”(《日本写真50年》,p.90)
《日本写真50年》封面
宣言中并没有“私写真”字眼,倒是有不少柳本尚规认为不同于“私写真”的“私小说”,怎么能变成“‘私写真’的宣言”呢?
更吊诡的是,荒木经惟在《写真的话》(彭盈真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出版)里谈“阿幸”时竟说:“虽然很久之后才提出‘私写真’宣言,然而‘阿幸’其实是它的前身噢。”(p.29)“‘私写真’宣言”的注释是:“最早发表于《电通人》第一五八号的文章里:‘我有一个很老式的信念,认为只有真实之物才能够创造同样的真实之物。’[一九六五年]此外,《感伤之旅》的序文提到:‘我拍的是自己蜜月旅行的照片,但并不表示就是纪实摄影!这不过是以摄影家的身份捕捉爱情,又碰巧以私小说的形式开始罢了。我一直觉得这就是私小说,因为私小说和摄影的感觉最接近。’[一九七一年]这段文字可说是‘私写真’宣言的清楚标记。”(p.78)
《写真的话》封面
围绕《感伤之旅》,柳本尚规、饭泽耕太郎、大竹昭子、荒木经惟四个人的观点组成了一个相互矛盾的“私写真”与“私小说”怪圈:柳本尚规认为《感伤之旅》是“私写真”,不是“私小说”,“私写真”与“私小说”不一样;饭泽耕太郎认为《感伤之旅》是“私写真”,《感伤之旅》里的宣言是“私小说宣言”,“私写真”与“私小说”一样;大竹昭子认为《感伤之旅》是“私写真”,《感伤之旅》里的宣言是“‘私写真’的宣言”;荒木经惟认为《感伤之旅》“凑巧从私小说出发”,“私小说非常接近摄影”,并且他自己确实提出了“‘私写真’宣言”。
《感伤之旅》封面
另外,山岸章二将深濑昌久也牵扯进了“私写真”与“私小说”怪圈:“十年间,深濑持续拍摄自我暴露的状态,以显现摄影的真实性,或许也能称为摄影的私小说。”(《私写真论》,p.)“摄影的私小说”被饭泽耕太郎解读成“狭义‘私写真’”:“山岸在上段文章里所说的‘摄影的私小说’,指的当然是‘将镜头朝向自己与自己的家人’的狭义‘私写真’。”(p.)
中平卓马在黄亚纪编译的《写真物语Ⅱ日本摄影-》(重庆大学出版社年出版)收录的一篇访谈里表示:“私小说无聊的地方,是因为私小说的‘私’打从一开始就背负巨大主题,‘私’总是忧郁的、悲惨的、有着妻子却也有着情人——那些日常生活中狼狈不堪的就一定是‘私’的主角。我的‘私’和这种‘私’是不同的,我只对‘作为碎片的自己’抱持关心。”(《写真物语Ⅱ日本摄影-》,p.88)
《写真物语II日本摄影-》封面
中平卓马否认自己的“私”与“私小说”的“私”一样。因此,饭泽耕太郎形容中平卓马为“拍出了一连串分毫不差地符合了定义的‘私写真’”(《私写真论》,p.48)的人,就跟他“所谓的‘私写真’即是与‘私小说’一样”的观点相悖。
饭泽耕太郎自相矛盾之处数不胜数。
他认为拉帝格和石塚三郎的摄影作品不符合狭义的“私写真”定义的其中一个理由是感情倾向单一:“不管是拉帝格还是石塚,都能轻松透过照片牵引人们的欢乐或幸福感,但是他们必定都经历过的负面感情(如恐怖、不安、悲哀、愤怒等),则很难从照片中看出来。”他认为符合狭义的“私写真”定义的《感伤之旅》同样感情倾向单一:“书中出现的阳子,常常不苟言笑,以一种‘若有所思的沉郁表情’入镜。而荒木也细心地排除了阳子其他表情的照片。”(《私写真论》,p.)
他认为拉帝格和石塚三郎的摄影作品不符合狭义的“私写真”定义的另两个理由是表演性和二元性:“在他们摄影作品中的‘私我’,总是带有像在舞台上演戏一般的二元性。”
但他分析深濑昌久的“私写真”摄影作品时赞扬了表演性:“在《游戏》中,深濑明白率直地展现出他想捕捉的摄影表现手法。现实世界的虚构化,或是幻想的掺入,彻底的扮演与夸张过头的演技,对于持续溶解如泥般的物质感之执着,以及物体化身体的清醒视线,还有以性作为介入他人关系、充满狂放野性的现场,都在这本摄影集中表露无遗。”(p.-)“《游戏》可说是透过洋子的绝妙演出才会成立的‘私小说’。她丰富的表现力、瞬息万变的表情,以及仿佛完全进入另一个角色的能力,就像一个天生的演员。”(p.)
他评价中平卓马的随笔文章时强调了二元性:“我们可以看到‘我自己’与‘历史’或是‘社会’(有时使用‘世界’这种更抽象的表现称呼)的二元论式对立构造,而这种构造日后也如同强迫观念一样,渐渐支配着中平的思考。”(p.51-52)
最后,饭泽耕太郎指出拉帝格和石塚三郎的摄影作品缺乏真实触感:“想从镜头拍不到的角度看出完全纯粹的‘赤裸裸的我’,也只是一种虚构,但是我们仍然得说,拉帝格与石塚的照片中的‘私我’,仍欠缺完全对应他们人生的真实触感。”可缺乏真实触感竟是被饭泽耕太郎奉为“树立日本‘私写真’基准的决定作——《感伤之旅》”(p.)的“独特性”所在——“这本《感伤之旅》却也是一本经过充分捏造而成的虚构故事。荒木巧妙设置各种诡计,使得全作像是一本摄影集,并让读者对于‘私小说’中的情节信以为真。”(p.)“以‘私写真’角度来看,《感伤之旅》的独特性,难道不正是出于现实与故事间的虚实不明吗?”(p.)
感情倾向单一、表演性、二元性、缺乏真实触感,这些“条款”既能作为拉帝格和石塚三郎的摄影作品不符合狭义的“私写真”定义的理由,又能作为荒木经惟、深濑昌久、中平卓马的摄影作品符合狭义的“私写真”定义的理由。那么,狭义的“私写真”定义,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吗?
饭泽耕太郎毫不担心自己无法自圆其说,他搬出了广义的“私写真”定义,掩盖他对“私写真”的论述的漏洞。他评论深濑昌久和牛肠茂雄的摄影作品时彻底解构了狭义的“私写真”,将之引向广义的“私写真”——“只要拿起相机构成画面,被摄体就是‘我自身’的体现。超越了拍摄自己与身旁周遭的景致这种狭义的‘私写真’,‘所有的照片都是私写真’这个基本命题,似乎就在那里直接被实现了。”(p.)“尽管《在习以为常的街道上》并不是直接揭示拍照‘私我’的狭义‘私写真’,仍然与中平卓马的《为了该有的言语》一样,具有以拍摄者自身的身体性作为媒介,以完成等身大‘生命纪录’的视野。”(p.)“若将牛肠的摄影作品视为(不论在广义上或是狭义上的)‘私写真’,我们或许可以回过头来,体验一种生命与摄影间不断进行的奇迹邂逅。”(p.)
既然“所有的照片都是私写真”,“私写真”便是指“摄影”本身。故,广义的“私写真”等于“摄影”。此种情况下,饭泽耕太郎解构了狭义的“私写真”,“私写真”这个词便失去了存在价值,被“摄影”完全代替。至于所谓的“纯粹私写真”,则是“纯粹摄影”——“一种我=摄影=世界的超现实关系”。
可见,《私写真论》是一个荒唐的文字游戏,饭泽耕太郎任性地独揽制定游戏规则大权——“若要追问为什么一定要举这四位摄影家,有点难以回答,只能说是凭着摄影评论者的直觉判断:我认为这四位摄影家的各自创作行为,正好都投射出了‘私写真’的可能性。”(p.7)他的研究不是建立在理性分析上,而是建立在直觉判断上。
他绕来绕去,想探讨的无非是摄影者的“自我”在摄影中的体现:“‘私我’的轮廓与内在,也都会随着时代与环境,而产生剧烈的变化。尽管如此,我们似乎仍然可以从摄影作品中的‘私我’的呈现倾向,推测出各自特征的存在方式。这时候与其说是探求‘私写真’,更像是探索摄影这种表现媒介的特质。”(p.)
虽然顾铮在《中国私摄影论》中也定义了广义的“私摄影”和狭义的“私摄影”,跟饭泽耕太郎如出一辙,但“私摄影”和“私写真”却截然不同。“私摄影”的“私”是“私”在中文里的意思“与‘公’相对、不公开的”,指“私欲”、“私情”、“私生活”等,不同于“私”在日文里的意思“我”:“私摄影,作为相对于公共流通领域里的摄影类型,私生活与私人性的生活感受成了其主要内容,同时也包括了拍摄这一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私生活性。”(《中国摄影批评选集》,p.)“私摄影的一个区别于其他形态的摄影的重要特征是,拍摄者的镜头只指向自己的私生活或一定圈子内的生活,是在相对封闭的空间中展开摄影,对于一同分享这些影像的人,摄影可能同时兼有娱乐与行为的功能。”(p.)“一旦私摄影获得与人分享的可能,私将不私,则此时私摄影的亚文化甚至反主流文化的特点就将消失。”(p.)
所以“私摄影”是“不公开的摄影”,不是“私写真”(“我摄影”)。
顾铮论述中国的“私摄影”时,采取了跟饭泽耕太郎的《私写真论》相似的结构(除去“前言”和“后记”,正文分为“历史与发展”、“摄影家群像”、“再谈‘私写真论’”三部分)——第一部分“私摄影:世界摄影史的谱系”裹挟了一些外国摄影师(刘易斯·卡洛尔,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雅克·亨利·拉蒂格、凡·德·埃尔斯肯、荒木经惟、南·戈尔丁、琼·斯班斯、长岛有里枝、蜷川实花、沃尔夫冈·蒂尔曼斯);第二部分“私摄影在中国”论述了“私摄影”在中国的发展及中国摄影师的“私摄影”实践;第三部分“兼作结语的思考”归纳了“私摄影”的特点与局限性。
顾铮并没有在《中国私摄影论》里交代自己是否参考了饭泽耕太郎的《私写真论》,或者其笔下“私摄影”跟饭泽耕太郎笔下的“私写真”有什么联系,不过,他与饭泽耕太郎都提到了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雅克·亨利·拉蒂格、荒木经惟、长岛有里枝四人。
关于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顾铮认为他的摄影作品符合狭义的“私摄影”定义:“美国摄影家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去世后,留下了他拍摄的画家奥基芙的底版多达幅之多,其中包括了相当多的奥基弗的人体照片……而在斯蒂格里茨去世前,他本来是想要销毁这些底版的。显然,他拍摄奥基弗的初衷,只是为了他们两人的私情。”(《中国摄影批评选集》,p.)饭泽耕太郎则认为他的摄影作品不符合狭义的“私写真”定义:“然而像是亚佛雷德·史提葛利兹、爱德华·威斯顿、哈利·卡拉汉、W·尤金·史密斯,或是生前持续以鸟取砂丘为舞台,透过独特构图拍摄各种群像照片的植田正治(~)……等,在这些摄影家拍出的自拍像或全家福照中,让人感受到直接反映出拍摄者人生的‘私写真’要素其实非常稀薄。”(《私写真论》,p.28)(“亚佛雷德·史提葛利兹”即是“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
关于雅克·亨利·拉蒂格,顾铮认为其摄影作品符合狭义的“私摄影”定义:“而法国人雅克·亨利·拉蒂格,作为一个富有的银行家之子,他拿起照相机,除了作为一种消遣手段之外,也有为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生命中的三个妻子记录她们的日常举止的想法……而拉蒂格的将家庭日常作为摄影题材的做法,实为私摄影的根本。”(《中国摄影批评选集》,p.-)饭泽耕太郎则认为他的摄影作品不符合狭义的“私写真”定义:“不管是拉帝格还是石塚,都能轻松透过照片牵引人们的欢乐或幸福感,但是他们必定都经历过的负面感情(如恐怖、不安、悲哀、愤怒等)……拉帝格与石塚的照片中的“私我”,仍欠缺完全对应他们人生的真实触感。”(“拉帝格”即是“雅克·亨利·拉蒂格”。)
关于荒木经惟,顾铮认为他的摄影作品符合狭义的“私摄影”定义:“在私小说的国度日本,荒木经惟是当之无愧的私摄影大师……荒木经惟拍摄于年的《感动之旅》,记录了他与阳子的新婚旅行,但奇怪的是,这场旅行的影像却始终披着一层死亡的阴影,而且不幸的是,当阳子于年去世时,这部作品似乎成为了他的私人感情的一言成谶式的作品。”(《中国摄影批评选集》,p.)饭泽耕太郎也认为他的摄影作品符合狭义的“私写真”定义:“荒木从一九六〇年代后半到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之间的摄影作品,尤其是他实质上的第一本摄影集《感伤之旅》,宣示了日本‘私写真’的诞生。”(“荒木”即是“荒木经惟”,《感伤之旅》即是《感动之旅》。)
关于长岛有里枝,顾铮认为她的摄影作品符合狭义的“私摄影”定义:“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少女摄影’,最初是一些女大学生用摄影的方式拍摄自己身边的人事,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的看法……这其中出现了不乏才华的女摄影家如长岛有里枝、蜷川实花等……”(《中国摄影批评选集》,p.)饭泽耕太郎也认为她的摄影作品符合狭义的“私写真”定义:“即使长岛是九〇年代辈出女性新锐摄影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影像的表现上,她不仅发挥了灵巧的驾驭能力,也相当清楚自己与现实世界间的关系,并不断摸索新时代‘私写真’的可能样貌。”(《私写真论》,p.)(“长岛”即是“长岛有里枝”。)
尽管荒木经惟与长岛有里枝是狭义的“私摄影”和狭义的“私写真”的交汇摄影师,顾铮与饭泽耕太郎却仍未达成共识:荒木经惟的摄影作品符合狭义的“私摄影”定义的理由是包含了“私人感情”,符合狭义的“私写真”定义的理由是“过去一直被隐藏的‘私我’,在这时候以如此明朗的样貌公诸于世,在当时带来现今也无法想像的冲击”(《私写真论》,p.);长岛有里枝的摄影作品符合狭义的“私摄影”定义的理由是“拍摄自己身边的人事”,符合狭义的“私写真”定义的理由是“相当清楚自己与现实世界间的关系,并不断摸索新时代‘私写真’的可能样貌”。
顾铮提到了日本是“私小说的国度”,以荒木经惟为桥梁暗示了“私小说”跟“私摄影”的联系,可他没讲“私小说”跟“私摄影”有什么具体联系。饭泽耕太郎的《私写真论》倒是讲了“私小说”跟“私写真”的具体联系,并且,在日文里,“私小说”的“私”跟“私写真”的“私”都是第一人称代词“我”。
最巧的是,饭泽耕太郎定义狭义的“私写真”时说狭义的“私写真”类似“家庭相簿”,顾铮定义狭义的“私摄影”时说狭义的“私摄影”包括“家庭私人照片”。
各种证据证明,中国的所谓“私摄影”脱胎于日本的所谓“私写真”,顾铮的《中国私摄影论》脱胎于饭泽耕太郎的《私写真论》。但顾铮不仅不交代“私摄影”的来历和出处,还把日文里的的“私”(“我”)篡改成中文里的“私”(“与‘公’相对、不公开的”),把荒唐的“私写真”篡改成更荒唐的“私摄影”。
*****
摄影与诗歌文艺是你内心的生活态度
摄影·诗歌·艺术·电影·音乐
转载请注明:http://www.popkd.com/wadzz/65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