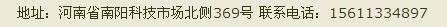我在精神病院见到的那些病人
有一天,我问了医生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假如出于某种意外,我们被人当作病人误送进了精神病院,那该如何向医生证明我们没病呢?
医生像看个白痴一样看着我以为我在开玩笑,但他很快就发现,我问得很真诚,而且不但是我,周围一圈小伙伴同样一脸真诚地仰望着医生等待答案。
为什么会问这么狗血这么白痴的问题呢?
医院医院,也就是说我并不是在精神科,而是在精神病院。每一个新收进来的病人,都会做精神检查,其中有一项很重要:自知力。这个自知力的检查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
你是谁?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那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这里吗?
那你觉得自己有病吗?
我对这种假想出来的困局百思不得其解。病人都说自己没病。可是,换了我,该怎么答呢?若直接说有人陷害我,硬说我有病,把我送进来的。这不是活脱脱的被害妄想症吗?
7年前,我走入心理咨询师这个行业,至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在每日书里写下的这一组故事多数来自在临床学习的经历,故事或许悲凉,但故事里的人未必悲凉。
01
/患癔症的女人/
今夏酷暑,医院了,理由很直接:太热,路上辛苦,实在懒得跑。但那天还是顶着高温预告又一大清早穿越大半个城来跟着医生出门诊了,机会难得。
医院还是老样子,一早人多,上了年纪的老病人们通常喜欢赶早过来开药,顺便和医生聊会天,当然也极有可能是倒过来:来和医生聊会天,顺便开个药。如果没有初诊病人的话,等到十点来钟,就会稍微空闲下来一些。其实,我们跟门诊的,并不想空闲,最好忙碌些,如果再多几个初诊病人那就更好了,因为可以有更多的学习观摩机会,虽然那样的话可能医生就会忙到过饭点儿。
今天还蛮清闲的,我心里嘀咕:早高峰结束得有点早啊。正想着,进来一个人,坐下了。
我眼前一亮:是她!
这个病人,我记得,大概两个月前她来初诊正好也是我在跟门诊。印象非常深刻,原因一她是单向抑郁,这在临床上比较少见,更多出现的状况是双相障碍,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躁郁”。
原因二是因为她长得好看。她是那种很符合传统审美的好看,鹅蛋脸,眉眼修长柔和,皮肤白皙,茸茸的卷发扎个丸子头,穿着干净T恤、七分裤、平底鞋。今天和那日完全的素颜有些不同:她抹了口红,且是那种非常鲜艳的红色。这一抹鲜亮的红,使得整张脸都明媚了不少。
复诊主要是开药,医生一边和她打招呼,听她絮絮地讲一些近况,一边就手开好了药,她拿过方子起身道谢出去了。
我趁着没有病人进来的空档,迫不及待问医生:她好转得真快啊,还不到两个月呢,居然已经有这么大的变化了。医生回头,正色看着我:你是怎么认为她的好转呢?
诶?这话什么意思?我一边想一边说:她看上去没那么憔悴了,说话声音也大了许多,脸上开始有表情甚至有笑容了,还有,她化妆了呢,口红颜色还那么鲜亮。
医生点点头,仍旧一脸凝重:但是你没有看到的是,医院大堂后才抹的!上次也是如此!你难道不觉得那口红有点突兀么?
我刚想说“没有啊,这个色号现在很流行的,就是要这种鲜亮的颜色才吸引人啊”,但猛地想到一点:她的病例上诊断是抑郁症,抑郁的病人通常不会如此在意自己的形象,即便有需要也不会选择这么鲜艳吸引他人注意的口红颜色。
这种带着明显诱惑意识的举动,显然和她的状态对不上号啊。
想到这些,我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医生见我有些明白过来的样子,继续说:你看着,她等下拿了药肯定还会进来的。
果然,她又回来了。复坐下,欲言又止。
“医生,可不可以再帮我开张病假条?”她略带些不安地开口。医生倒是爽气,直接问:“还是一个月?”
她点点头,轻声说:我在准备回去上班了,已经有别的领导跟我谈过了,说我愿意的话可以帮我换个部门。还有,我现在回我爸妈家住了。
医生停下笔,抬头看她:“哦,那你是已经把事情都告诉他们了?
她摇摇头,吐出一个字“没”,就红了眼圈,略平复了下,又说:我就说妈妈身体不好我住回去照顾一下。单位里的事情我不打算告诉他们了,如果能换个部门那应该就会没事了。我也没想到会有别人也了解这个情况,这次是那个领导主动来问我的,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情况,要不要换个岗位。
医生听完说:“这样也挺好。不过单位的事情解决了可以不用说,家里的事情总归也是要面对的。回去住一阵子就好了,住久了你不说你爸妈猜也会猜到的。药接着吃,打算回去上班前再来复诊一下。”说完,把开好的病假条交给她。
接过病假条,她犹犹豫豫地站起身,说了声“谢谢”,然后似乎有些不太情愿地走了。
太反常了啊!我内心的问号都快要满溢出来了:医生对她明显有些严厉啊。这太不是医生的风格了。
还有,这个女人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和初诊见她的感觉不一样了呢?
其他几个门诊见习看着我的样子好奇心也被吊起来,医生看着此刻反正没病人,干脆就地教学了。
“你见过她几次了吧,那就说说你觉得她是什么问题。”医生对着我说。
“不是抑郁吗?”我有点不敢肯定了。
“那你还记得她初诊的主诉吗?讲给他们听,大家讨论一下。”医生带着些许莫测的笑意。
“睡眠不好,情绪低落,将近一年。每天想到要进单位还在路上就开始心慌、胸闷、手脚发麻。”我边回忆边说,“最初怀疑是肺气肿,到医院就诊治疗过一段时间,后来有医生建议看精神科,怀疑有可能是抑郁。但一直没有去看,直到出现严重睡眠障碍才来的。”
旁边的小伙伴听了不由自主“咦?”
“性骚扰。”医生补充:“病人自诉,在单位遭遇性骚扰,程度可能不止骚扰。”
一群跟诊学习的小伙伴们听得有点懵,相视无言,完全讨论不到点子上。
医生只好直接给了答案:“癔症。”
啊,突然有一种混沌天地豁然开朗的感觉:她的肺气肿、她的抑郁症状、她的快速好转、她的口红以及她自诉的生活经历,都被串联起来了。
02
/对爱情妄想的芝姐/
芝姐是东北人,论外形颇有点五大三粗的意思,黑而壮(体重的问题和她长期药物治疗有很大关系),不过收拾得还挺干净,头发梳得齐整,病号服也都穿得妥妥贴贴的。可能离开东北很久了的缘故,口音并不重。她其实和我同龄,我私下奉她“姐”,是因为当年她真的是个混江湖的大姐大。
这样的一个芝姐,十年前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分裂,然后就一直反反复复中。
当医生第一次向我们介绍芝姐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圈儿人都懵了个云里雾里,从社会功能、家庭关系、身体状况到精神状态,芝姐对我们的提问有问必答,绝无虚言。听完一圈,我们傻眼了:没毛病啊!家庭和睦,工作顺利。身体精神是有些状况,但离精神分裂貌似还远着呢。
可芝姐觉得自己有病,她说她犯病的时候,会心痛!痛到仿佛心在被撕裂,痛到什么都做不了。她在描述那种痛到时候,有那么一瞬间,看着她的表情,我的心仿佛都“啾”地抽痛了一下。
心痛是真的痛,但肯定不是因为心脏有啥毛病。
人的精神真的是很可怕,它无法承受的时候就会拖上躯体一起来分担。有时候我们会生病会各种不适,说到底就是精神的需要。
那芝姐为什么需要“心痛”呢?因为她的“求而不得”。
芝姐患有钟情妄想(更准确是钟情和被钟情,通俗的说法,就是花痴)。她想象着一场旷世奇恋,一场心有灵犀的爱恋,一场历经磨难仍忠贞不渝的爱情。
她爱上了她的上司,一个比她更有能力,而且看似“懂得欣赏她”的男人。所有日常工作中很正常的沟通接触,所有旁人闲谈时的只言片语,在芝姐一系列的病态的逻辑加工后,铁板钉钉地成为对方跟她示爱的表现,甚至连对方不堪纠缠后的责骂驱赶,在芝姐看来都成了爱的考验。
她“深信”这份爱情坚贞不渝,无法动摇。和这样的爱情相比,生活如此平庸,相濡以沫的老公全然不被她放在眼里。
但一切都是虚妄的,只存在于芝姐的想象中,在她的想象世界里,有无数关于这场爱恋的美好点滴,而且只有她知道。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只有芝姐知道的真实。
芝姐曾经因为严重的妄想驱使,坚持和老公离了婚,因为她要证明给那个人看:我愿意为你做一切事情。
离婚后芝姐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知道真相后的老公又苦求着芝姐复婚,然后就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医院看病住院的,她是那种很信任配合医生的好病人,但是,她是来治疗“心痛”的,她可不觉得那些“妄想”是病。也就是说,芝姐觉得有病的,我们认为没病。我们认为有病的,芝姐觉得没病。
芝姐不太愿意讲她的爱情故事的原因,不是因为怕别人觉得她有病笑话她,而是认为“你们都不懂,懒得和你们讲”,所以我们就齐齐被带坑里去了。
你知道吗?当芝姐讲她的“爱情故事”的时候,她的笑容如此甜蜜,恍若少女。
虽然现如今,她是他们那个圈儿里小有名气的TopSales,但她在为生存挣扎的岁月里所经历的事情恐怕除了她自己无人能够知晓。半辈子靠着近乎原始本能的力量搏杀在生存场的芝姐,在她分裂的世界,有一个最纯粹、最女人、最接近美好人性的故事。
我突然觉得这样也挺好的,病就病吧,也没什么不可以。
03
/小萝莉/
精神疾病的鉴别诊断是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不仅需要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更要有清晰严谨的逻辑思维体系,这一些凭我们这样的短期旁观见习是很难训练出来的。但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因为旁观的身份,我们往往比医生们更
转载请注明:http://www.popkd.com/wazz/14718.html